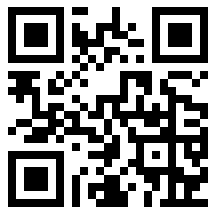新华社首位领衔记者张严平的人物报道集《时代面孔》近日由新华出版社出版。这部作品集与众不同之处在于,读者阅读它时会不知不觉间眼含热泪。这种共鸣来自张严平的文字描述,更为准确地说,源于她发自内心的情感输送。
“记者这个职业最让我迷恋、让我神往、让我一直停不下脚步,正是因为它让我有机会走进一个又一个优秀的、高尚的、平凡而伟大的心灵之中。让我领悟着生命的意义,感受着民族的灵魂,只要我的生命还在,他们就是我一生的珍藏。”张严平在一篇《记者心路》中写道。
将自己的感动化为千万人的感动
人物报道是张严平投入最多气力、最深情感的新闻实践。从她笔下,走出了王顺友、郭秀明、陆幼青、杨业功、白芳礼、张云泉、华益蔚、吴大观、王争艳、申玉光、傅宝珠等典型人物,报道发表后在全社会产生广泛而积极的影响。
长篇通讯《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——记优秀共产党员、木马县马班邮路乡邮员王顺友》发出后,有读者在新华网上留言:“这才是民族的脊梁,这才是汉子!你潮湿了我的双眼!”长篇通讯《我的“中国心”——记报国有成的党员专家、中国航空发动机之父吴大观》发出后,一位在媒体工作的读者感慨:“第一次读科技人物的稿子流泪了。”长篇通讯《走不出雪山上的那双眼睛——记养路工陈德华》发表后,四川省交通局的一位女同志给张严平打来电话说:“我们是流着泪读完了你的稿子,看那个标题就感觉和你的心可近了。”
事实上,张严平在采写这些典型人物过程中也在流泪。她采访王顺友时跟着他骑马走在山峦交错、古树遮天、山道越来越险的原始森林里。她在采访手记中写道:“我大气不敢出,两手紧紧地抓住马鞍,脑子里不断闪念着一个念头:万一马踩滑了怎么办?万一……会死吗?马终究没有‘万一’,它把我驮了过来。那一刻,我流泪了。不是为自己,而是为王顺友。在这样一条生死路上,他一年走330天,走了整整20年,而且还在继续走着。”
类似这样边采访边流泪的情景,在张严平身上发生过多次。她说:“感恩记者这个工作让我把一颗被点燃的心掏出来,化为一颗火种,燃烧在我采访的一个个人物之中,向更多的人传递生命与心灵的火焰。”
对此,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黄传会认为:“能将自己的感动化为千万人的感动,这是一个记者的莫大的幸福。”走进受访者的内心深处的张严平,能够感受到“王顺友们”对她说的“你写的,我看了。你最明白我心头”的分量。
曾任新华社总编辑的南振中评价张严平:“30多年间,她倾心于发现生活中各类具有感染力的典型人物,在采访过程中她的心被典型人物点燃,化为一颗火种,然后通过新闻作品向更多的人传递。这是‘感染力的传递’。”
好报道来自“原生态”“笨功夫”
写出具有感染力的稿子,记者首先不要怕辛苦。张严平主张记者要勤用眼、勤用嘴、勤用腿。简而言之,就是采访、采访、再采访;理解、理解、再理解。
她在回答一位记者同行提出的“为什么你就能写出好的报道来”之问时曾说:“我的体会是,在采访时伸出我所有的感官,包括心灵,就像老树的根一样,深深地扎入大地,收获原汁原味的东西,然后再把它们消化了,在写作的时候通过我心灵的每个毛孔释放出来。因为带着生活的原态,又有了心灵的激荡,所以写出来的东西肯定就不一样。”
这种被张严平称为“原生态”的采写方式,让她吃了很多的苦。在汶川“5·12”大地震现场,为采访青川大山里的两兄弟,张严平与同事们在陡峭的山道上驱车3个小时,中间涉水闯过一条河,再徒步攀爬两个小时,他们采写的《明天,太阳照常升起》因而感动了无数人。
在采访江苏省泰州市信访局局长张云泉时,张严平和他本人谈、和他身边的人谈、和他帮助过的人谈,甚至和对他有意见的人谈。不仅如此,张严平还特意到信访局的信访窗口体验了一天,深切感受到这活儿真累。她问张云泉:“张局长,我在你的窗口待了一天了,那是一个很让人头疼的地方。你一天到晚都在这个被不愉快的事、负面的事、有阴影的事包围的环境里工作,这个环境对你有没有影响?如果有影响,那是什么样的影响?”
“他愣了一下说:‘没想到新华社记者会提这么个问题。’”张云泉用“模式”回答不了,便说,“每天回到家里后,头都要炸开了,回家的前一两个小时,妻儿们不要跟我提任何事,一提就发脾气、拍桌子。”
“他讲得很真切,这是那些‘模式’包容不了的。这些真心话,你得进入到他的生活里才能听到,才能理解。如果你对他一无所知,又问不到点子上,这些‘活鱼’就不会‘跳出来’。”在张严平看来,采访一个人,不要依赖已有的资料,而是要走进他的内心深处,感受他的所思所想。这种被张严平称之为“笨功夫”理念,让她收获到很多的“独家新闻”。
张严平分享写人物报道的“诀窍”是,把每一次采访都当作第一次,不漏一个线索,不漏一处地方,不漏一个人。“最好的文字是最朴素最有味道的文字,而不是花里胡哨地卖弄。谋篇布局不是绞尽脑汁的问题,而是深入采访后水到渠成的结果。”
难忘稿子背后的“大编辑”
在《时代面孔》一书中,张严平多次提及自己稿子背后有“大编辑”们的辛勤付出。在新华社,一直有个十分重要的传统,就是对一些重要稿件,总编室要召集有关人员进行“头脑风暴”,对稿子“会诊”。这些参与“会诊”的人就是记者张严平眼中的“大编辑”。
何谓“大编辑”?张严平认为,“大编辑”普遍具有高于记者的政治水平、思想深度、境界情怀、文字修养,常常使得一篇如粗糙毛坯的稿件焕发生机,甚至在看似无望处抓到星点火花开掘出新的生命。
这从张严平的一篇题为《大编辑》的记者心得中可见:她曾在时任新华社社长李从军的指导下写过《走向希望的春天》《永恒的召唤》等稿子。曹绍平、刘思扬、张宿堂、唐小可等,都是让其领悟很多、学到很多并给予她最大发挥空间的“大编辑”。其中《索玛花儿为什么这样红》这篇荣获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稿子,是由时任国内部主任张宿堂连夜精心修改、编辑签发的。
“人们通常会认为,已经经过部门编辑看过的稿子最后送给领导审阅签发,领导在上面画个圈、签个字就可以了。但是,我经历的新华社两任总编辑南振中、何平从来不是这样,送到他们手上的每一篇稿子,他们都会从头至尾逐字逐段地精心修改。”张严平记忆犹新,比如《写给英雄母亲的信》的标题替换了原来概念模糊的《英雄泪》,让这篇稿子有了目光深挚的“眼睛”;《一位老人与300名贫困学生》的标题替换了原来空洞的《他有颗太阳的心》;《用爱点燃爱》的标题替换了原来的《“麻风村”的爱心使者》,使得人物内涵有了本质的升华。
“回望我的记者生涯,每一篇能留下的稿子,无不渗透着稿子背后的那些‘大编辑’的心血。”张严平发自内心地感谢道。
在感恩“大编辑”们的同时,张严平说,日常生活中的自己生性内向、不善言谈,但命运偏偏给了她一个挑战,让她成为一名必须和很多人打交道的记者。“不知为什么,只要一面对我的采访对象,面对那一个个我视为一座矿、一座山、一本书,有待于去寻找发现他们内心的人,我就进入了一种通电的状态:兴奋、好奇、敏锐、思维活跃、悲喜同身。”
如今的张严平已经退休,《时代面孔》一书对她自己而言是记者生涯的一个小结,对新闻同行而言是一种交流学习,对社会和读者而言是又一次“共情传播”。
“我热爱记者这个职业,不但采访者给了我动力,读者也给了我动力。”张严平说,记者需永远脚踏实地,俯身朝下。